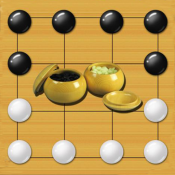风俗视角:另类的盛宴-阴魂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华夏江南一带都流传着一个神秘而另类的盛宴——阴魂盛宴。传说在这一天,阳间与阴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亡灵们可以重返人间享用人间美食。无数家庭会在这一夜准备丰盛的宴席,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菜肴和水果,以招待“返乡”的亡灵。这个盛宴融合了生死、人神、现实与超自然的元素,是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传承与思想表达。
伦敦城的塔玛拉,总会问围墙里的天地过客: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就要为我唱响那同一首歌。命定的旅人:爱。
木头人,可我从未听你唱起那首歌。
我的童年,我的一生,我的乞讨对你来说已是最美的赞歌。
你的分离,你的荒诞,你的勤奋可是这还不够,薪水的护城河上仍缺少一枚用你的尸首制成的徽章。

“在那高高的逼仄的塔上住着美丽的女皇塔玛拉:她像天国的天使般美丽,又像恶魔般狠毒而狡猾。”莱蒙托夫,“塔玛拉讲话的声音: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希冀,其中包含着全能的魔法,还有着某种莫名的权力”。
善恶、道德修饰的黄昏雕像,在暗夜中为负重的过客敲着熟悉的丧钟。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古堡使人沉迷于狂欢与乐观的幻术,“这种一切都往好处想的乐观态度也是一种病态”。铺展开来的亮丽的林场--刑场--木屋,遮掩了深埋于地下如锁链沉重的病的根须。
爱国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区别就像蜜蜂与马蜂,后者是踩在前者的尸体上靠这主义吃饭的。
在一团漆黑的洞窟,搔弄萤火虫一样的微光魔术,不知这些东西跪拜的是王冠还是金杯。
托洛茨基:“以情绪激昂的爱国主义者身份登台表演的‘荣誉’和‘灵魂’的骑士不仅叩开了盟国使馆的大门,而且有时还领到了政府的津贴”。
寄生虫的化妆师,断翅遁地的鸟蛆,“你们的墨水瓶内一点刺鼻的胆汁也没有——而只有不干不净的污水。”
侃侃而谈的慈眉善目而又精于投机的救世者:奶牛,托洛茨基:控制火焰的方式,不过是感到烫手便把手缩回去。
托洛茨基,“政治力量的分野不是在根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和次要问题上更公开和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上车!大家都上车!”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负重驮畜受虐之死描写王者的盛宴,“它拉得动大家。我要抽死它!”
现实是一个病态的梦,冥河污水的浓度和真实程度超出了观察者远观的评估。
浑身插满针线头的牛马,既在“治病”又在被吸血,每一根抖动的丝线都传递着恐怖符咒的催压进而在边牺牲边拯救的梦幻迷雾中剜肉取食。
受刑之人,“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罪与罚洗刷的虔诚足迹隐瞒着死堡的位置与深层骨制成就,头戴金铁帽子的伪善阴魂: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这话我爱听,尤其爱听你--祈祷和做梦者--说还有梦。
画师的梦,功在黑鸟。鸟语:这就是命。
渔民:离水鱼,别怪我;被天气弄丢的鱼肉,一切原因的上限都是天气的错。
在生态环境方面,于理直气壮中听到了天谴的老调。受灾受祸合理、有理,从何而来?自然气象的异常,用科学的口气讲出来一个作为上天“谴告”的必须承受的陈旧故事,以这种现象那种现象的新衣服迷惑人们的双眼,实则是腐烂之地的潜形遁地术。
多么有趣的天气,背负着人间的地狱。按照此理,总而言之:受极端天气影响,墨西哥毒贩的活动有所增多,而美国人则悄悄地躲到了猎场的背后用学术天气撰写动人的剥橘子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理不会溜走,而生活却可以被凝滞”。一群皮影站在白色帷幕后面,动静皆是戏。
真理站在原因--别致的谎言--面前,死于科学郑重其事的宣判。
脏扫把扫屋子,越扫越脏。结了不少蜘蛛网的屋子,只是没有更名宣告为“盘丝洞”的勇气。
揪出那些以色列人,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加沙灾变将不幸之人架在火山口上料理熏烤。
可怜的小玉米,爆米花一锅接一锅的炸出来,还带着香甜的牛奶味,品尝着伤痛和悲剧的残忍乐祸口感是活人的特权,一秒种的权力与快活盗取了玉米的记忆而为非人之物装填了一种畸形的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剪断了玉米与爆米花的联想与记忆,并把它们摇进到压力炉内转圈圈。
拉尼娜和厄尔尼诺,被时代的小丑迎接出来的两位改头换面的“新神”,贩子一提到它们行将出场,连防晒霜--隐形鼻环--的销量都会加倍提升。简明的骗术:现象作为结果,被小丑拿来当做解释人间所言之物的原因。
在夜里手握水晶球的占卜术士不知何时学会一种新语言:科学调查,这种调查只是为了给吃菜品的人寻找一个合理的免除罪责的理由。
尼采:真理取决于你的视角。视角取决于锤子的原始痛苦和反抗精神,以及能够对照出病态的阳光和健康状态的认知。
观众也是错位的演员,有趣的误会使其暂时坐在看席上。头顶掠过神奇的飞斧,总会有一把劈面相逢。历史车轮上面绑着的人,战战兢兢地配合一场又一场惊魂的喜剧,于飞斧的呼啸中唱响自愿的骄傲掩饰下的不得不爱的赞歌。
吕克特说,“你还要像虫子一样缩做一团,在敌人凯旋车轮下忍辱偷生”?
斗牛士的挽歌:征战为士,归来为畜。父亲骑在儿子的功头上,想当臃肿肥恶鸟巢的第二书记。为父者持子功自居,公开谏言通信而指点施令自然引起奴隶头子的反感,一手埋葬了苗子吸收养分的前程。一半急功近利的无边界钻营,另一半忘恩负义的捍卫边界的果断舍弃,两者在豪情万丈的牺牲中讲述着甜蜜而脆弱的共同事业的联盟,爱古堡者在极端扭曲的世袭垄断的吊桥上撞的伤痕累累并粉身碎骨。
资本缝隙里的理想斗士与圣徒,窒息挤压变形。信仰的导师参与了资本的谋害。
春天有故事,但没有属于你的果实。吕克特,“鲜花盛开的春天不能给你的,秋天还会给你重新带来”。
乞丐的心里始终装着废品堆成的乞一奉十的圣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攥紧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一个卢布,坐等‘公众的幸福’的降临。等“死”,一个宏大的目标彻头彻尾成了死的形容词,那个被建筑起来的幸福花园不过是有朝一日体面的等死,如此而已。
几个华丽的丐头走在摧毁板凳的路上斗志昂扬,到了神庙却在刀光剑影间玩起了抢凳子的游戏,那叫一个凶狠。这游戏的获胜者,赶紧给凳子刷了一层金刚漆,嘴里喃喃低语:有本事,我叫你们来砸个够。
围着权力的尾巴欢蹦摇尾,这就是鸟人活动家自称的学问。扭曲匍匐,爬行乞乐。在这里,鲍曼: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泥潭里泥鳅,自成一派,与鼹鼠和鲶鱼的区别在于还没学会打洞。高贵者的小洞是通向神圣密道的捷径。
当论功行赏成了一句赐死的黑话,谁能逃脱认真的悲哀。卫城的蛇蝎搜寻卑微的有功人涂抹毒液,毒物的脑袋里只有一种语言:小心守夜的功贼突破承袭罔替的壁垒。阴魂的盔甲和帽子都是铁的,而凡人却是肉的。
归来的猛士,在转身凯旋的时刻胸膛被偷偷戳进了一把刻着世袭罔替暗记的刺刀。
活着时不能给你的荣华,死后却给你一座华丽的墓碑。吝啬鬼嘟囔着:就连着墓碑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价归宿,而我却为你施舍了如此之多,真叫我心痛。
一群在泥浆中只有说谎才能活下去的长鼻怪,捍卫着用鼻子的长度枕压的等级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后宫被爱戏弄地已经没了人样,要人的伪善道歉仪式和爱的承诺有何用:彰显残酷阴魂的博爱和仁慈。
一次次愚蠢而又贪婪的失误和牺牲隐含着科学特殊的献祭仪式,悲伤的眼泪成了养病的药引子,这病要人哭个不停。虚情假意的道歉为沉默的羔羊预谋下一次最为经济的死刑,死神的仆从把兑现谎言的日子推进了死的深渊。意外而又必然的刑场,终结了对病态的以缺陷为食者的追问。
如果科学是屠夫手里的一把宰牛刀,它还会得到牛的崇拜吗?看着用人的生命扭动科学严谨的发条,你以为的严谨中暗藏着多少烹羊宰牛且为乐的食谱。医学黑洞,远超地心引力。
阴魂制造了最强最大最惨的悲剧,却以悲观主义的诬蔑来否定任何对这种悲剧的真实描绘:哪怕只是一点现象。